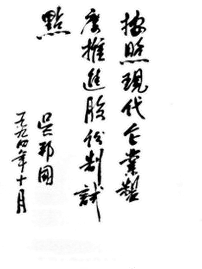一.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它是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手段和大目标之间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既需要全局性的精心合理的预谋和确定,又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
就国家对外关系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或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早期那些可称雄才大略的统治者,还是伊丽莎白一世、黎塞留、克劳塞维茨、俾斯麦、马汉、列宁、毛泽东或邓小平,都是大战略的杰出实践者或思想家。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明确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研究领域或分支,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可以说迟至20世纪50和60年代才明确出现。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一书内,根据他提出经典的战时大战略概念长篇论说大战略,涉及到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的、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关系。
哈特提出大战略经典概念及其初步理论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1976年爱德华•勒特沃克发表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在经典史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阐说了大战略的某些根本问题;1982年约翰•加迪斯发表《遏制战略》,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大战略范畴和命题;1986和1987年,彼得•帕瑞特重编40余年前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使之在当代保持为最重要的大战略论著之一,勒特沃克则发表具有广泛影响的《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大战略研究显著扩散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有: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和阿瑟•斯泰因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着重指出并且阐析了大战略研究的一整个基本方面;威廉森•默里等人主编《缔造战略》,为大战略理论提供了从古至今一整系列经典史例研究,并且展示了先前忽略或看轻的种种层面或维度;杰弗里•帕克以其杰作《腓力二世的大战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大战略史论著;约翰•伊肯伯里发表《胜利之后》,对冷战后西方的大战略根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和富含创新的理论性论说; 9.11发生后至今,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讨论更是方兴未艾,可谓构成美国国内辩护和批判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类政策精英舆论的首要内涵,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为加迪斯2004年发表并引起广泛反响的《突袭、安全和美国经验》。
在新的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中间,贡献最大的大概是战略史家兼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加迪斯。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遏制战略》、《大国的 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等)标志性地代表了大战略研究在哈特之后的重大发展。新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的最主要新贡献在于提出、论证和例解:大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也应适用于平时;就大战略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大战略问题的基本范畴和机理获得了非常显著的丰化和深化;大战略研究的时空范围得以极大地扩展,大战略理论由此更为充实、准确和有说服力。近几年来,大战略一语及其理论和政策实践研究已经频繁地见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战略和对外政策思想界,表现出新的重大的理论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我国,关于大战略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研究(连同对于西方大战略理论思想的介绍、研究、评判和借鉴)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重要进展。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尚处于很不充分的状态,系统的理论阐发、理论创新性构建和作为基础的大战略史研究尤为薄弱。不仅如此,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的、甚至不少是根本性的忽略和肤浅,需要予以补充、深化乃至升华。与此同时,在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对外战略问题领域,从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出发所做的思考和研究,连同精湛、连贯和高度自觉的对外大战略论说和相关的政策体系倡议,依然不多见,或者说尚未跟上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愈益引人注目的 战略实践的优化和创新,并且为之较充分地做出战略理论研究可以做出的一定贡献。因此,基于已有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成果,针对上述几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去从事关于大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这种研究的根本框架或纲要,除了从理论和战略史角度论证一个根本的前提即大战略的根本意义外,主要在于同样从理论和战略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更全面、更深入地界定和阐明大战略的以下基本问题及其内在机理(最笼统地说它们分别存在于大战略目的或目标、大战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大战略决策机制和体制、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艺术才能及领导素质这六个方面),其中不少是现有的大战略理论忽略的,另一些则仍然在国内外现有论 著内缺乏较充分和较深刻的论说:
(1)大战略为之服务的国家根本目标是大战略的头号问题,即大战略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国家根本目标的合理确定方式以四项要素的正确界定为主要内容: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可供使用的各类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追求某种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与其代价和获益比较。
(3)国家根本目标的应有素质,特别是战略性素质,概括地说就是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内在平衡和充足;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
(4)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对于“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包括力戒“问题被分割为各个组成因素……极少重视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过程的痴迷遮掩了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沉溺于手段导致忽视甚而败坏目的”;不允许战略决定战略目标,不允许手段毁掉目的;与此相关,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
(5)国家利益和目标(特别是若干重要甚而至关紧要的利益和目标)的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的确定。它意味着“战略集中原则”,要求确定国家多项重要目标的大体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坚决地将关注重点和努力重心放在、并且保持在由此决定的最优先最重要的事项上,并且为此对所有其他目标、利益和事项打上合适的“折扣”。在实现战略集中的前提下,尽可能力求做到“战略内在连贯”,即战略集中与战略兼顾的平衡。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战略平衡是大战略的根本精髓。
(6)优良的大战略一般需要有关于如何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深思熟虑、细致系统和表述良好的战略规划。
(7)“目的与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它主要涉及按照手段或能力定义目的和目标,以达到对大战略而言差不多最为重要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关于手段,必须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在所涉问题上的可用能力、关于能力或手段的现实与关于它们的想象,必须注重节省资源问题——在确定目标、大战略、战略和作战方式等各方面节省资源有巨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与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的还有内涵丰富、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的对称性战略vs.非对称性战略问题。
(8)可用的不同类手段或资源的确定,连同更重要也更困难的不同手段间的平衡。就前一方面而言,特别重要的一是提防忽视或轻视其中某一或某一些类型的手段或资源的危险,二是突出主要的一两种手段的必要,三是开发、动员、指导、协调和使用它们的正确方式。就后一方面而言,往往最关键的是政治 与军事、经济与军事、外交与军事之间的大致平衡,为此必须对所有手段打上各自适当的折扣;与此同时,每一类手段涉及的各项基本任务也需尽可能实现内在平衡。
(9)诸种手段的应有素质。特别是应当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包括国防体制、军事体制、兵力结构、指挥结构、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思想和信条、武装部队人员素质等),应当有怎样的外交(包括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和信条、外交操作素质和外交人员素质),是否有和应当有怎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就此最重要的一是拥有还是缺乏对外经济战略,二是它是否有较高的自觉和内在整合程度,三是它是否与大战略的其余组成部分大致平衡。)
(10)大战略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即大战略必须有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支持,必须有同样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际上的吸引力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可接受性,否则不仅缺乏追求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两项必要的大战略手段或资源,而且毁伤特定的大战略本身的生存和贯彻。
(11)对于政策行为之结果的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要有较为全面的力量对比、胜负对比和成本效益评估,从全局观念出发将每个局部和在这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们恰如其分的地位;不仅如此,这种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有时需要是有足够长时间尺度的历史性的。
(12)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优化。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拥有优良的大战略的最重要保障。有了这种优化,才有决策、政策行动结果评估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必须有集思广益的讨论和提议,也必须有高效的协调,连同集中决策和统帅领导;与此同时,由于“官僚机构”往往阻绝战略眼界、创新和灵活性,需要努力将此减小和限制在可能的最小程度上。
(13)大战略思维方式,特别是包括反映大战略本质的全局观念、敏锐坚定的“分寸”或平衡意识和宏大的远见。大战略思维素质需要富有特征的大战略式教育。
(14)大战略是关于目的和手段及其关系的艺术;大战略“艺术创造”依靠才能和实践,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然而与此同时,大战略(特别是大战略目的)也需要具有哲理基础、内在连贯和得到清晰表达的基本原则。与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密切相关,具有其特定要求和特征的“大战略领导素质”问题极为重要,且其内涵异常丰富。
(15)形成大战略的困难与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的绝对必要。“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就此必须充分理解和牢记环境动能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必须在难以预料地变化的形势中进行战略调整以求适应,还必须为难以避免的受挫或失败可能性留有余地,并且为此规划替代性选择或“退路战略”。
三.在特别根本的认识论意义上,上面列出的大战略思维方式和大战略艺术本性问题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在此有限的篇幅内,它们值得予以较深入的谈论。
大战略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反映大战略一大本质的全局观念。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个整体,在战争中甚于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必须从观察整体的性质 着手。丘吉尔对大战略也有与此相同的一项基本理解,并且用下述特别精彩、特别凝炼的话语去表述之:“单一的观念统一”(a single unity of conception)、“全景视野”(a full view of the picture)和“分寸”或均衡意识(sense of proportion)。这位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度的战略决策参与者、又是关于此次大战的大史家和战略评判家的著名人物相信,在1914至1918年,“作为一个整体的战 争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互不关联的立足点上被牵引的。战争并非僵硬呆板地分成各个部分:分成法国、俄国和英国等各个盟国,分成陆上、海上和空中,补给与战斗人员,宣传与机器装备等;它事实上只是在一个既定时期里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和压力的总和。”然而——他的完全合理的苛评是——它被予以支离破碎地处理。因此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西方惨祸和战略蠢举的一大教益在于,“在研究、思考、指挥和行动达到即使不完美的统一以前,必须有经年累月严酷的教诲。 ”同样,在他们主持的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的授课纲要内,保罗•肯尼迪与其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教授同僚强调大战略是个非常总体性的概念,需要有全方位眼界 和大图景。必须抵制所谓专门化倾向。大战略或治国方略要求其执掌者同时思考许多事,或者说需要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洞察力或见识:“与倾向于沿我们的X对Y轴或我 们的四联矩阵出现、甚或在我们的驾驶员座舱电脑显示屏上出现的相比,天地人间的事情更繁多更丰富。”
大战略思维需要较为长远的历史眼界即宏大的远见。俾斯麦曾说,一位国务家所能成就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仔细聆听上帝的历史步伐,拉住他的神袍摆边,同他一起在历史的道路上走上几步。这就是宏大的远见——俾斯麦珍视的一种思想必要和他相信的一种认识可能,尽管他显然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有清醒甚而谦恭的理解。聆听上帝的历史步伐意味着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去透视当今,去设想和思考它的较长远的未来构造和走向,并且由此构思大战略路径。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具备长远的眼界,意味着研究大趋势和预料可能性,并且在可行限度内以平衡当前需要与长远 需要的大战略方式操作相关的实践或实践准备。这方面,一项往往至关紧要的必需在于区分紧迫的眼前挑战与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避免一心关注前者而忽视或轻视后者。它之所以往往是至关紧要的必需,很大程度上缘于一种政治或治理常态,用一名美国前副国务卿的饶有体验的话说,在于政府领导人员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 “内箱(inbox)”的俘虏——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被紧迫的眼前要务支配,而这“内箱”依其本性并非总是给所有要务留下等量的空间,那些并非表现为日常火急之事的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太经常地被挤出议程。没有宏大的远见,到头来就难免只是应付事态而非塑造事态。
大战略思 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着相应的特殊智识素质,亦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内在大联系,产生富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设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其功能主要在于拓展一个人的眼界 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这种教育“更多地基于心灵开放的程度,连同它生成的积极的思想努力”;这种教育应当“产生战略的决策者、规划者和咨询者,其专门本领更多地由对复杂问题的精致把握和影响大事态的能力去标志,而不那么由狭窄的知识、神秘的技术和操作细节以及对权威的忠顺服从去界定。”
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和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克劳塞维茨一向强调,战争及战略操作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他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将战争比作绘画,将战争研究比作绘画研究。他在一篇很可能是1806年撰写的文章中说:艺术是一种发展了的能力,如果 它要表现自己,它就必须有个目的,并且必须有旨在实现这个目的的种种手段……将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就是创造。”在如此界定艺术(如同战略)的本质和根本要素即目的、手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之后,这位异常杰出的思想家接着说:“艺术是创造的能力,而艺术理论教这结合,在概念能够这么做的限度内。因此我们说,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才能——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实践。”这说得何等简洁,又何等准确、深刻和透彻!
本着同样的哲理,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第三篇第一章内直接和较具体地谈论了战略本身:战略包含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 非常容易;“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保罗•肯尼迪在其主编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开篇内如此演绎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旨在维持和增进国家长期最佳利益的大战略努力充满难以预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偶然性障碍;它不是契合约米尼传统的一种数学,而是契合克劳塞维茨灼见的一种艺术,永不可能精确无疑和事先注定。如此的、本质上是艺术的大战略依靠什么?“依靠对政治实体的目的和手段作不断的和明智的再审视,依靠克劳塞维茨……最尊重的两样无形的东西——智慧和判断力”,而智慧和判断力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
海权论创立者兼战略理论大家马汉在许多场合可谓教条主义者,像约米尼那样相信“不变的科学战略原则”。然而即使如此,他的某一些论著仍包含着与约米尼的教条大相径庭的优秀见识。他在1897年出版的《纳尔逊的一生》中,写出了缘于形势的能动性和不确定性而 来的两样东西——优良判断力的必要和精神勇气的意义,那似乎出自总的来说比他深刻得多的克劳塞维茨。他写道,鉴于偶然性的重大作用和某些时候冒险行事的必需,僵硬刻板的决策可能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危险的。“约米尼之坚执原理的明确公式化无疑可被认为多少过于绝对,过于书生气。”一方面是即使最精致复杂的理论也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实践的往往无法预见的要求:靠什么去填补这两者间的深沟?靠优良的判断力的行使。马汉在远不如他的《海权论》那么享有盛名 的上述著作中强调:“为了在战争中获胜,必不可少的补充即智力把握和洞察是一种精神力——那使得一个人能够信赖内在的光辉即拥有信念,一种在最为巨大的紧急情况下控扼犹豫、支撑行动的力量。”马汉在此指的首先是勇气:为其结果不确定并且可能殊为可怕的冒险行动承担责任的勇气。
在一定程度上,大战略艺术中的这类关键成分也可用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两个根本概念来表述,那就是“美德”和“命运”。马基雅维里将一切真正和至高的价值都集中于他所称的“美德”(virtù),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取自古典传统和人文主义的含义,意在表述某种充满活力的、自然赋予人的东西,即英雄主义和追求文治武功之伟大成就所需的力量。马基雅维里确信,在无神的自然世界中,人除了他自己以及自然赋予他的能力外一无所有,只靠这些去和同一个自然行使的致命力量作斗争。“命运”(fortuna)对“美德”便是他对这形势的解释。如果屈从于只能听天由命的感觉,就会是缺乏“美德”;一个人必须振奋,开河筑坝去抗争和制约命运的洪流,因为人的行为只有一半受命运支配,而另一半或近乎一半是留给人自己主宰。在此,仍然可以回到本节援引得最多的克劳塞维茨,提及他独特的“天才”(genius)概念,即为了尽可能且尽多地克服不确定性、不可预料性和意外困难等 等而创造性地运用智力和情感力。简言之,大战略艺术的精髓就是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大战略”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对怎样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及其它类型手段来实现国家(外部)安全目的而进行的筹划和指导。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研究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的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 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也往往都是从国内因素中来寻求解释,而这点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大战略研究的首要贡献。
以结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是忽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这点很大程度上恰恰提示了以技术因素和地理环境间的互动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结构理论”与大战略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研究一直深受肯尼斯•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由于沃尔兹创立的实际上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因而这种影响在促进大战略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弊端也使得大战略研究普遍都带上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缺陷——研究者往往忽视对国家大战略运作环境的考察。
沃尔兹最初力图创立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这种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对沃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体系都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任何体系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及单元间的互动”。据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完 全是集中于单元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时也处于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对沃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只是一种通过了解整体各部分的性质及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种理论的根本前提是假设在国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它的因果关系。国家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的事实则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且受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此简化理 论无法对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解释,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正因为两个层次的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因而沃尔兹认为要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首先必须将两个层次的变量区分开,然后再考察这两种变量间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但由于沃尔兹将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和考察这种结构产生的效应上,因而就构建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言,沃尔兹仅仅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即他真正构建的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解释的只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沃尔兹理论的这一根本特征集中体现在其核心要素,即均势自动生成论中。
沃尔兹从他的理论构架中推导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他认为,这个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秩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这个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产生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国家为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以维持实力平衡;其次,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还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来平衡那些在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沃尔兹阐述的这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手段,即“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最终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均势反复和自动地生成。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限制作用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的反应,但他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能够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结构产生的约束力,同时也取决于单元自身的特点。沃尔兹的理论只表明为什么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果要解释各国具体反应上的差别,就必须展示出各国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沃尔兹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他的理论解释的对象只是“体系性结果”(即均势最终会生成),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即国家总是会制衡那些构成霸权威胁的国家)。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进程”的主要成果,沃尔兹实际上建立的乃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这种理论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源自亚当•斯密并经过保罗•萨缪尔森等学者改造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沃尔兹理论中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根本效应的界定和阐述,正是建立在“ 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市场”的类比基础上。然而,沃尔兹提出的这种类比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市场逻辑得以形成的诸种要素全都是流动性的,而作为国际政治体系 基本构成单元的国家则根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流动性,即任何国家的地理位置完全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不仅是“非历史的”,而且是“非空间的”。因此也就造成了那些以结构理论为研究指南的大战略研究在关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状况的同时,普遍忽略了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 的潜在含义,而这些恰恰是构成国家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核心成分。由于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解释的主要是体系性结果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因而以这种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对不同国家大战略环境上的差异一般都忽略不计,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能够作为干扰性变量而存在,但这类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 理论的内在逻辑。对这类研究中出现的异常现象,研究者们一般都是从国内因素中来寻求解释。就当代大战略研究而言,这种缺陷集中地体现在当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中。
“离岸平衡”与美国大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的权势分布从两极结构转变为单极结构。与这种结构转变相对应,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讨论。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但参与这场讨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美国将放弃以往的那种“绝对优势战略”(Preponderance),转而追求某种“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美国将摆脱冷战期间在欧亚大陆承担的主要义务。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水体阻碍力”使国际体系中任何大国都无法获得全球霸权,大国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区域霸权国,而区域霸权国则将会阻止其它地区的大国获得区域霸权,即区域霸权国相对于其它地区必然将充当起“离岸平衡者”的角色;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追求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实质上 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战略,这不仅因为任何形式的霸权都将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过度伸张,同时也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其它国家(尤其是大国)迟早通过扩充实力或彼此结盟的手段挫败这种对霸权的追求。“离岸平衡”实质上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战略,即首先由相关地区大国来承担起制衡潜在的区域霸权国的责任,只有当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凭自身力量有效承担起制衡责任时,另一个地区的“离岸平衡者”才会介入其中。据此,“离岸平衡”要求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及早退出欧亚大陆,以便使相关的地区大国自己承担维持本地 区的稳定与和平的责任,只有当欧亚大陆再次出现霸权威胁且相关的地区大国无法进行有效制衡时,美国才有必要重返欧亚大陆;而一旦达到制衡目的,美国则将会选择再次退出。
然而,离岸平衡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美国决策者的遵从。冷战后美国虽然减少了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但美国仍然在欧洲和东亚的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美国主导欧洲事务主要政策工具的北约不仅在持续得到巩固和扩大,而且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加强自己对东亚局势的控制力,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已完全超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对这种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出现的异常情况,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典型做法就是从国内变异中寻求解释,而这点正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大贡献。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美国霸权大战略上的代表性成就,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雷恩新近才提出的“区域外霸权理论”,这个理论同时兼容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前者构成美国扩张的许可性条件,后者则解释了美国霸权的动机。这个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修 正派外交史学家提出的“门户开放学说”,即美国之所以要寻求区域外霸权并不是出于客观的安全需要,而是出于美国特有的门户开放式的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从严格意义上说,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结构理论框架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结构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够根本弥补结构理论的内在缺陷,反而在理论上会造成许多原本没有的问题,因为这种形式的修正不仅损害了结构理论的简约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而后者也就意味着结构理论正在演变为一种“不断退化的研究纲领”。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的霸权动机来解释美国的霸权行为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这种论证非但无法弥补结构理论的缺 陷,反而有可能使最后的研究结论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作为从沃尔兹理论的框架中衍生出的结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的探讨虽然都考虑到技术因素(核武器)和地理因素(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大战略的潜在含义,但由于这两种因素在结构理论中都只能作为干扰性变量,因而 “离岸平衡”依赖的仍然是沃尔兹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及由此推出的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在面临他国 权力增长或霸权威胁时,其行为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追随”(Bandwagoning)。沃尔兹阐述的“均势自动生成论”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想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如果我们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么我们就必须展示出“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到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 最终究竟是否会采取制衡行动,不仅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状况是否发生了严重失衡,同时还必须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不是决定对这种失衡做出必要的反应。[18] 沃尔兹对他的“均势自动生成论”做出的这个规定,实际上是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一个无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相关国家没有采取制衡行动,那么他总是可以将此归结为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沃尔兹以后的结构理论家力图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结构理论 的缺憾,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严格地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因为将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中的做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来证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在面临他国权力增长或霸权威胁时必然将采取制衡的行动。
地理政治与“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终结
作为当今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基础,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就在于缺少某种内在的时空维度,因此也造成了那些以结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大战略研究在关注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状况的同时,普遍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大战略的潜在含义,后者正是地理政治学关注的主题。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地理环境与国际权势竞争间关系的科学,地理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不仅在于它力求要达到一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总体认识,还在于它关注的主要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局势,即地理环境虽不会经常发生改变,但它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性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后者正是由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间的互动造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推崇的“离岸平衡”虽然考虑到海洋国家的地理位置对美国大战略的潜在涵义,但都忽视了技术发展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影响导致“离岸平衡”对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而言并没有多少实际的相关性。
“离岸平衡”实际上是利德尔•哈特界定的“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翻版。“英国式战争方式”就是指依靠海权,并同时使用海上封锁、财政资助和 外围作战的手段,而不是凭借一支大规模的陆上远征军来战胜欧洲大陆上的敌人。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英国为盟国提供的财政补贴和军事供应,二是英国针对敌人的脆弱部分进行的海上军事远征。[22] 哈特认为,这种大战略是节省、适度并且是有节制的。而这种大战略的关键就在于,英国享有的制海权足以确保其任何对手都无法通过入侵英国本土的方式从而将有限战争转变为无限战争,且英国的战争目的主要也不是彻底打败敌人,而是为获得某些实际利益,这些利益“一般是殖民地和海外领土”。结构理论推崇的“离岸平衡”同哈特主张的“英国式战争方式”两者间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两种大战略都主张,作为主导性海洋国家,美国或英国在平时应尽力避免卷入大陆事务,从而将维持区域性稳定与和平的责任推卸给相关地区大国,在战时应尽力避免大陆战争,而主要利用海权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压力和外围作战方式 来打击敌人;其次,两种大战略的成功实施都依赖两个前提,一是主导性海洋国家有充裕时间集结资源应对大陆事态的变化,二是主导性海洋国家可以在不承担任何实质性大陆义务的情况下彻底打败敌人。作为对英国传统大战略实践的总结,“离岸平衡”与“英国式战争方式”可能都不乏合理成分,但如果将这种由历史类比中得出的结论应用于解释和指导美国在二战后和冷战后实行的大战略,则根本忽略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互动对大战略的潜在含义。
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英国在大部分和平时期确实一直尽力避免卷入大陆事务,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商业、贸易和殖民地事务上,而这点也正是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实行的光荣孤立政策的由来。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在18和19世纪绝大部分的和平时期中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不仅是由于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而且也在于技术因素决定了那个时代中的战争仅仅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有限战争”而不是“绝对战争”,而这种有限性“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人力是有限的,也因为那些不断变化的战争目标同样是有限的”。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主要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进步及由此造成的其它变化使英国根本无法继续推行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而这正是英国之所以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的主要原因。英国在进入20世纪后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转而置身于大陆事务,关键就在于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 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作用彻底地改变了英国传统大战略的运行环境。首先,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岛国地理位置赋予英国安全上的传统优势,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英国为自身安全所需要的防御范围已不再止于英吉利海峡而是必须向欧洲大陆纵深拓展;其次,技术进步使大陆国家的潜在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并因此造成了战争性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有限战争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战争。这种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大战略运行环境的变化对海洋国家的大战略的影响就在于,首先,海洋国家要维持优势地位就无法继续脱身于大陆事务,因为大陆均势同海洋国家自身安全间的联系已变得无法分离;其次,战争技术和战争规模的变化使海洋国家根本没有充裕时间来集结资源以应对大陆事态的不利变化,因而海洋国家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干预大陆均势的发展。
“英国式战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某种对英国大战略实践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之所以在历次重大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它掌握了制海权,而且也在于它愿意从事并实际主导了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由于自17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敌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大陆强国,因而英国根本无法指望以海上战争来击败它们,尽管海权在20世纪以前的技术条件下确实可以保障英国的生存,但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 海军的价值是极为有限的。当英国仅仅将战争努力局限在只动用海军力量和小规模陆军时,它一般是不成功的,“只有当英国远征部队在战争期间转变成一支能够并愿意进行针对其欧洲大陆对手的重大战斗的大陆野战军时,英国的干预行动才会是决定性的”。与这种错误相类似,哈特提出的“英国式战争方式”必须要承担的另一种风险,是海洋国家一旦被迫暂时性地退出了大陆后,是否还有望重返欧亚大陆。尽管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国家都是在暂时退出欧亚大陆后又再次成功地返回,但现代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类似“半岛战争”或“诺曼底登陆”那样的两栖作战几乎没有了成功可能,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言,“承诺在距离最近的战区、以当时资源能够允许的最大规模来支持某个大陆盟国的义务,非但不是同英国传统战略相违背,反而恰恰是英国传统战略的核心。由海权提供的灵活性肯定也会使其它的行动成为可能,例如殖民征服、贸易战、对盟国的帮助、小规模两栖战役等 等,但这些行动不过是陆上战役大决策的辅助手段,且这些行动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如此。其次,当我们确实要诉诸于某种纯粹的海洋战略时,这种做法并不是某种由自由选择或返祖智慧带来的结果,而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这种做法是一种必须的战略而不是选择的战略,是一种生存的战略而不是胜利的战略。 ”
|